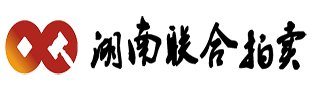香港纪伯伦国际拍卖行—瓷器工艺品百瓷集韵香港纪伯伦国际拍卖行—瓷器工艺品百瓷集韵
文化遗产界一直有种争论,到底是修旧如新还是修旧如故?为此《奈良宣言》《苏州宣言》学界都在喋喋不休,永无止尽。现实界,各种实验和建筑改造实践都在诠释这种或那种试验性的改造与创新。
古代文人生活慢而雅致,今人都在试图模仿和再现。于是前些年茶道盛行,茶器衍生的各种有关茶的文化趣味,造就了相关工艺的复兴。但是,热闹之后,生活终究是平静的,仿佛文本华美都是虚浮在茶汤上的浮沫,并没有太多人在真正钻研其中的门道,也少有人真正在用器过程中体会匠人的用心和极致生活的乐趣。
何为金缮,又何为锔瓷?前两周的京都工艺展青年论坛中,国内工艺界网红的两位匠人就此议题,谈道论艺了一番。
从技法而言,“金缮”与“锔瓷”都是对破损陶(瓷)器进行修补。修补陶(瓷)器,日本叫金継ぎ,中国叫锔活。从历史来看,日本修补史追溯到室町时代(1336年)中国修补史则可追溯到宋朝(960-1279年)。彼时,修补是对器物的一种态度。两国因为对美学的理解和哲学态度的差异,造就了对物的观念的差异,这种文化的差异就体现在这两种手艺里。
无论锔或缮,从经济生活的角度来看,当器物损坏,工匠通过修补延长其实用价值并形成一种行当,都是工艺成形的本初愿望。一方面日常用器价廉,锔活能够延长器物的生命。另一方面,在中国文化里,人们对待缺陷时具有两面性的。一则常有一种刻意规避的心态。一旦当东西坏了,就要遮盖、要修补。甚至即便事物本身已经支离破碎,但我们往往会制造一种圆满的假象,避而不谈。此处,破镜重圆是一种心理需求,也就可以理解!二则,圆满又是国人的人生要求。每逢重要的场合和高价值的工艺上,完美无缺的器型才是陈列的中心。而锔活仅是修补损坏的器物,功能大于审美,并不能摆上台面。
邻邦日本的文化却是呈现的是另一种美学精神。它有一种基于对残缺的崇拜态度。以日本茶道为例:缺陷、简素、枯槁、自然、幽玄、脱俗、静寂,所谓不完善的、不圆满的、不恒久的残缺,在他们看来都是唯美。因为这里头包含了朴素、谦逊、自然的意思。理解金缮在日本的工艺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具体从工艺种类来看,金缮日语中称Kintsukuroi(きんつくろい),是为用金修补、整治。本意所言的以金修缮,是指用天然的大漆黏合瓷器的碎片或填充缺口,再将漆的表面敷以金粉或者贴上金箔。金缮源于中国漆艺中的泥金工艺,明代黄成所著的《髹饰录》一书中,便有“补缀:补古器之缺”的文字记载。但检索现代工艺文献,我们并没有关于这门手艺的后续记载。因为它逐渐发展,虽成型于中国髹饰工艺中的泥金工艺,但从工艺呈现上并不完全沿用古法的制器规则(补漆法原本起源于中国,本质上是属于漆艺的范畴,但在工艺作品中却不会去表现器物的残缺),而是成为属于邻邦东瀛的器物修复术和艺术创作。邻邦日本人用黄金修缮的本意在于面对不完美的事物用一种完美的手段来对待。因此,金缮的核心,在缮而非在金。(对于修复器物,日本也有调朱漆或者直接保留大漆的黑色在裂痕上的传统。)金缮修复的适用范围甚广,除了瓷器和紫砂器,还有竹器,象牙,小件木器,玉器等,但主要以茶器为主。经过金缮处理的器物,因原器物本身的材质、纹饰、色泽不同,为此所呈现的美感也各异。虽然工艺上延续漆器传统,用金不是太多,但是金代表一种姿态、一种态度。
不同金缮师的工作风格迥异,致使工艺大致可分为随器修补、随色修复与随性创作三派。“随器”派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者,他们以恢复器物的使用、陈设等功能为第一要务,通过修补去延长破损器物的使用寿命、以或艳丽或沉稳的装饰去掩盖破裂痕迹。倾向“随色”修复的匠人,则注重恢复器物的审美价值。为了让被修复器物的外观更接近原器,有经验匠人通过调制出与原器物颜色相似或协调的色彩、以非常高明的绘制手法,让器物的破裂痕迹“消失”。而主张“随性”创作的匠人更像艺术家,他们与严谨的“随色”派相反,往往并不介意改变器物的外观甚至功能,为了追求特殊的视觉效果,“随性”派会将器物的原貌更改创新。
金缮主要材料是生漆和金箔(金粉、金泥),其中的生漆又叫做天然漆、土漆、国漆,故也经常被叫做中国漆,是一种天然树脂涂料。修复的过程是采用大漆和上瓦灰、糯米粉和蛋清,黏合器物的碎片或是填补缺口后,再在漆表面敷以金粉或金箔进行装饰。这一工艺发挥到极致,后被演绎成为莳绘金粉工艺。复原破碎的物品,对于匠人来说,也是一次全新的创作过程。金缮的本意在于面对不完美的事物用一种近乎完美的手段来对待。用世上最贵重的物质来弥补缺陷,意在表达一种面对不完美时的姿态,坦然接受,精心修缮,而并非试图掩盖。简言之,用朱合漆直接粘补,经过金缮后的器具上会有一条条纤细的金色线条,顺着瓷器受到冲击形成的裂纹流淌。应该算是漆器的另一种诠释吧!电影《silverlinings》里有句谚语:“每一朵乌云背后都镶有金边”,用此语解释金缮这门工艺,恰是十分契合。
锔活的修补方法不一样:“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说的就是要用金刚钻钻孔用锔钉抓牢修补工艺。锔,北方也称锔活儿,也有粗活细活之分。粗活一类,也称常活,是走街串巷的手艺人挑着担子吆喝着上门修补破损的碗碟。这类锔活儿是为修补生活用品,其目的是节俭而不追求美观。因而锔钉粗大,工艺上略显粗糙,基本为铁钉修补。而另一类的行活锔匠(也称当活)在古董、古玩行里有一席之地,则是专门修补大户人家的观赏瓷或紫砂壶等。因对象本身就不完全是实用器,故而修补的手艺也就更要求精致,因此也称行活,或秀活。这时候锔钉会采用锻铜工艺,如果遇到独具匠心的匠人,锔瓷细活美妙绝伦,往往会使修补后的器物增值。
无论哪一种锔活,对受损的瓷器进行打孔,用像订书钉一样的金属“锔子”再修复的技术,其实器物还是受到二次伤害的。因为这种工艺是不可逆的!
因为,锔瓷工艺从工艺技巧划分,通常分为五步:第一,找碴、对缝,对破损的瓷器恢复原状,准备修补;第二,定位点记,结合位置和位点,计算锔钉数量和位置;第三,打孔;第四,锔钉;第五,用鸡蛋清和瓷粉调和补漏,防止瓷器漏水。历经多朝沿袭,锔补无论哪个门派都是采用锔钉打孔的方式。
清朝乾隆时期,单一锔补也转为锔补修复、嵌饰做件、镶包配饰等彰显匠人绝活技艺的专门行当。各种花钉、素钉、金钉、银钉、铜钉、豆钉、米钉、砂钉等锔钉纷呈,造就了明清之后瓷器、紫砂、石器、木器等锔补藏品的丰富面貌。如今在茶器上的锔活基本就是沿袭这一路风格。

就技艺本身的功用和难度,锔钉和金缮应是不分伯仲,还各有千秋。据匠人邓彬实践(在两种方式都尝试了之后)发现:用锔钉修补将碎未碎的冲线,比金缮更加牢固;而如果瓷器缺损,比如碗口缺了瓷,或者茶壶断了嘴,就只有依靠金缮的手段,用木胎和大漆按原样造出型填补上去了。故缮与锔,应是两种不能完全互相替代的修缮方式。就技艺本身而言,锔和缮并无高下之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好比补牙。采用不同的材质,去到不同的牙医诊所,得到的治疗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锔聚合和,器物的好坏与新生,全凭匠人的手上功夫深浅与创意高下。
一件完美的瓷器破碎了,成了一堆瓦砾。面对这样的不幸遭遇,在茶人看来,尽最大努力用心修复,不仅是一种惜物态度。更是对匠人的尊重。器物因此际遇得以涅槃重生,器物的不完美因为人的“完美手段”而再次臻于完美。锔缮不仅仅是在物理意义上重新修复了一件瓷器,也是在美学意义上重新诠释了一种“无常之美”。
认真觉得有些认同。面对缺陷不去试图掩盖,反而以坦然心态去接受生命中的这份不完美,是对无常世界中的永恒的致敬。反之,只有珍贵的东西,才需要修补。不然的话,坏了的物体也就让它回到自然的状态的去吧!这种理念也没有什么错处。
但愿生活中的诸般不美好皆可以温柔对待,或者亦能别开生面。
所谓重拾破碎而不失尊严,抚平伤痛却有新欣喜
这一年,香港纪伯伦国际拍卖公司不仅保持了传统板块中的优势地位,同时在拍卖门类方面也勇于创新和尝试。得力于广大藏家和各界朋友的大力支持,实现了稳中求胜,众多活跃的资深藏家直接参与竞拍,保证了成交率,同时也出现了不小的惊喜。不少主题与特色专场竞争激烈,成交远超预期,新买家积极参与极大地提升了市场的信心,促成了更多的中档价位作品的成交。特别是古代书画作为纪伯伦的优势项目,许多重要稀缺的作品大都是领域中最资深的藏家直接参与。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大量新鲜血液注入,不断为市场带来了新的发展和活力。
2018年,是纪伯伦国际成立的第九个年头,布局未来,面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进步的艺术品拍卖业,纪伯伦始终坚持诚信、专业的经营理念,并且不断寻求正规化、企业化的发展方向,力图把纪伯伦国际拍卖行打造成国际艺术品交易的一流平台。